《嫩牛盗墓》46。
为了治好瘸腿师傅,我离开师父下墓赚钱,没想到我那师傅竟然雇了道上有名的黑瞎子要把我带回去。我再次睁眼时就发觉不对,黑瞎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。我下意识站起来环顾四周,眉头紧促,这节骨眼上他乱跑什么?站起来的动作太猛,我一下就头脑发昏,本就感觉涨的不行的太阳穴更是突突直跳,脑袋好晕,怎么回事?不会是黑瞎子给我做了手脚吧?
不对不对,我摇了摇脑袋,试图把这种想法晃出去。我不该有这种想法才对,我要是认定一个朋友,就算到死都不会怀疑他,这是对朋友的信任,也是对自己的信任。
我扶着墙费力的抬头,就看见刚刚还没踪影的黑瞎子就站在不远处,见我看过来神秘的一笑。随即他摸了下墙,好像触发了什么机关。一旁的石壁上突然显现了一个口子,里面多了一盏灯。黑瞎子点了灯,蓝绿色的光晕在黑暗里闪烁,照的他脸上的笑容无比诡异。我觉得这人真是神经,没好气的问道:你又搞什么飞机?
黑瞎子没回答,举着灯朝一旁的石壁照了照,上面居然显现了一扇门。我敢确定这块石壁先前绝对什么都没有,现在这又是怎么回事?我往前走了几步,见肩膀的伤没什么大碍,对着黑瞎子喊:你怎么知道这里有机关?黑瞎子依旧只是笑。
这时候我已经察觉不对劲了,忙上前几步,不曾想黑瞎子一把拉开墙上那扇门,一下就闪了进去。我心底突然涌上一股莫名的恐慌,我直觉这扇门后面不是什么好东西,黑瞎子不可能不知道,而且也不会这么没分寸的就跑进去。

可是他现在就在我面前进了这扇门,那只能说明说明黑瞎子早就知道这里有扇门,现在还抛下我一个人进去了,那么他想要得到什么?我几乎难以相信黑瞎子会骗我,心口说不上的难受,我只能大口大口的喘着气以延缓这种状况。
我闭了闭眼,还是决定开门。门一打开,一股热浪几乎就是扑面而来,里面是火,一整个房间里全是火,大火几乎点燃了一切,热浪席卷了我的身子,烫的我几乎要落泪。
我没看见黑瞎子,却看见了地上那块铁牌子,那是黑瞎子平日里挂在胸前的,我不受控制的走了进去,脚下松软的触感让我晃了神,有一瞬间甚至以为自己在地面上,可是心情却说不出的难受。
我慢慢的靠近那块铁牌,铁牌在高温下已经融化了不少,可是我依旧能看出,这就是黑瞎子身上的那一块。那他呢?黑瞎子呢?无尽的恐慌和绝望吞噬着我的理智,垂在身侧的手发着颤,他死了吗?他会死吗?烧伤的地方似乎已经没知觉了,这个问题一冒出来,我的脑袋就只剩下一片空白。
随即到来的是巨大的空虚,我只能慢慢的蹲下来,在一片火海里,用着发颤的双手轻轻抱住自己残破的躯体,慢慢把脑袋埋进腿间。不重要了,已经不重要了,师父走了,现在连你也要抛下我,都不重要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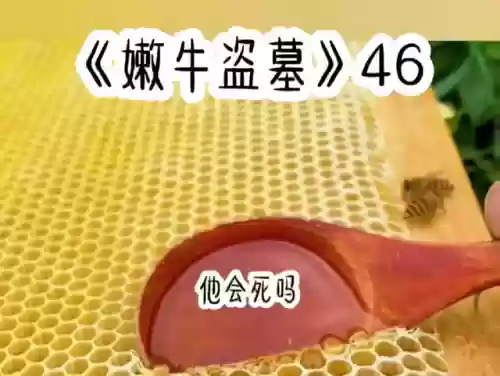
冰凉的触感在一片滚烫里尤为明显,我下意识拽住,在一片模糊中抬眼看去,那是那块铁牌,我一瞬间就汗毛竖起,这块牌子不是融化了吗?我警惕的望向四周,发现什么门,什么火海,通通都是空气,面前的只有拎着铁牌在我眼前晃的男人。
见我望过来,还惊讶了一小下,随即笑了出来,您可算醒了,我下意识吸了口凉气,你不是死了吗?男人眉毛一扬,什么时候死的,我怎么不知道,一起来就咒他,这小孩真是无法无天了,我却是松了口气,脑子里依旧一片混乱,我揉着眉心只觉得后怕,我什么时候睡着的?
黑瞎子收回铁牌挂回脖子上,随即蹲下来,两手撑着膝盖盯我,你刚怎么回事?喊你你不醒,眼睛里都没光了,要不是你脉象还算稳,我都以为你挂了,哪能那么容易挂。我拍拍脑袋,这么说我刚才没睡着,你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,眼泪鼻涕糊了我满手,你说你睡了没?黑瞎子觉得好笑,便道:看样子还想把手伸过来给我看,我没空跟他扯皮。缓了缓神就跟他说了那个幻境,不曾想黑瞎子听完却是撑着膝盖站起身,叹了口气,表情有点严肃,那我们得走了。
我不明所以,抹了把脸上干涸的眼泪,看着他的目光带着询问:艮属土,鼻属火,火烧泥巴,上泥下艮,宿鸟焚巢,是这地方的东西在赶我们走,此地不宜久留。说着,黑瞎子朝我伸出手,笑着道:走吧,爱哭鼻子的大小姐,你才爱哭鼻子。

我把手搭上去,一下子就被拉了起来,不知道是不是中幻觉的缘故,我感觉自己有点脱力,顺势活动了一下筋骨,你还会算命。说着,我顺便看了眼幻境里的万壁,上面很平整,完全不见那扇奇怪的门。黑瞎子扔了两把枪,只留下一柄手枪和长枪,他正在数子弹。
闻言随口道:说不上精通,略懂点奇门小算。奇门八算,我咀嚼着这词里的含义,突然想起什么似的,这人似乎也姓齐,你是齐家人。黑瞎子把子弹装进弹匣,将枪插回后腰,闻言回头浅笑,只是齐家与我颇有渊源,我这三脚猫功夫还担不起这名头。
奇门八算,两指一掐,可知天文晓地理,干得都是些透天机的活。黑瞎子道:不知为什么,我从他的笑容中看到了一丝落寞。算命算命,算得准的一般都薄命,齐家人命数已尽,已经绝后了。黑瞎子看了看那片空墙,从这走,看着那面墙,那滚烫的感觉似乎近在咫尺。
我深吸一口气,废话,既然那不知道是什么的玩意让我中幻觉,就是想把我往这里引吧,那你还去。黑瞎子摸了摸凌乱的发丝,顺手捋直了些,桃眉笑道:这一看就是给你挖的坑啊。我活动了下脖子,没立即接这茬,只是看着黑瞎子棱角分明的脸,认真的开口:我觉得你有一点说的很对,我这人就是脑子肘子,别人给我挖坑我就爱往里跳。不等黑瞎子接话,我继续道:可是这次老娘不是去跳坑的,老娘是去把那挖坑的找出来打一顿的。要是搞鬼的那东西真在里面,那它最好藏得紧点,别被我找着了。

黑瞎子顿了一下,拍拍我的肩膀,笑得很开心,有长进。随后他的笑容渐渐收敛,我知道这代表他要说什么重要的事情了。若是你和之前一样,这件事我可能会在我们安全下来再同你说。
黑瞎子把身后的包提回来,在里面翻找着什么,我找到了一样东西。和你讲之前,你得有个心理准备,也希望你看到这东西之后的表现不要让我失望。这人的语气没多少说教的意思,但是他的话一出就让人有点压迫感,这是久经沙场的人自带的感觉。他们说话时会不自觉带上这些微小的口吻,却能起到最大的成效。
我决定说点什么让他宽心,结果一张口就是,我感觉自己强的可怕。话一出口我自己都觉得诡异,索性闭了嘴。黑瞎子轻笑一声,把什么东西塞在我手里。我低头一看,脑子嗡的一下,耳边就再也听不见声音。那是一截烟管,我熟悉的师父的烟管。
大概过了有几分钟,我才从耳边的嗡鸣声中缓过神,我抖着手去翻那个烟管,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平静些。一旁的男人忽地叹了口气,朝我伸出手,给我吧,还是不能操之过急。谁知我捏着烟管的手却向后一缩,避开了黑瞎子的手。我抬头,在男人墨镜中的反光里看见了面色苍白,但是眼神坚定的自己。

我平静了下来,我开始思考这个烟管落在这里的用意。两种可能:
·第一,是师父自己留下来的,为得就是确保我能够看见。
·第二,是汪晋故意而为,就是为了将他们引到这个地宫的深处,让我看到汪晋希望我看见的东西。
我估计这两种都有可能,那就是第三种可能性。师傅留的线索,被汪晋发现,并且处理过后就顺势留了下来。如果是这样,那么这个烟管里绝对不会有什么重要的信息。
我摸着烟嘴的地方,那里本该是有东西的,现在却空无一切。我比谁都了解我师父,恐怕真正的信息还在别处。你在哪里捡到的?我抬起头,神情是前所未有的认真。黑瞎子记忆力很好,带着我走到角落,指着罐子间的缝隙道:这里。我蹲下身开始翻找,按照设想,若是师父在这里扔下烟管,绝对会引起汪晋怀疑。所以这个地方必不可能是师父最先放下烟管的地点,肯定是汪晋摆在这里的。
突然想到什么,我走了几步,直到在那面墙前站定,转过身看着那些罐子。我拿着烟管,小时候师父爱和我玩一种游戏,叫做头壶。把罐子放在远处,自己站在墙下,手上拿小支签子,投进五根就能吃上晚饭,以此训练我的准度。我慢慢蹲下来,直到与师父的高度齐平。坐着轮椅的师父,自然不会太高,投的也未必会很远。

我闭了闭眼,在心底模拟着师父的力度和角度,手腕用力,烟管与罐子发生碰撞,清脆的响声令我心底那根弦松了松。我上前查看,烟管落在一个瓶子里,已经看不出花纹了,但是好在质地够硬,我这么一倒腾居然没碎。黑瞎子倚着墙,幽幽开口:外边那些考古队看到你这样估计得搞死你。
我哪管考古队,直接把罐子里的东西全掏出来。果不其然,随着烟管倒出来的还有一个玉烟嘴,我认得这个,这是我师父的收藏。若不是我找到,这东西会一直待在这暗无天日的狭小瓶子里,或许若干年后才会被发现。
烟嘴里塞了张卷起的纸,我摸着纸条的手发颤,我慢慢展开纸条,上边用着指甲刻了几个字:墙上点灯可出去,勿寻勿念。随即旁边又刻了个划得乱七八糟的东西,糊成一团。我蒙到手电筒上也没看出个所以然,但我直觉这是种生物。
我收好纸条和烟管,循着幻境中的记忆,去摸索墙壁上的机关。按到凹槽时,墙上一块砖是松动,接着里面的空隙就漏了出来,伸手进去摸索,我毫不意外的在里边发现一盏灯,上面的膏体是犀角蜡烛,难怪能看见不存在的门。
这个幻境的原理和暗示的东西,我已经不想再去思考了,我只是想搞明白,到底为什么汪晋这么执着于把我往里面引。我师父又为什么宁愿自己牺牲也要让我放弃探寻这个秘密。若是为了我好,我能理解,但并不相信,这大概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,那就是跟汪晋所做的事情有关系。

我点燃了犀角蜡烛的灯,莹绿色的光晕渐起,照亮了眼前的石壁。我忽然觉得眼睛有点酸涩,不知是不是遇到过幻境的原因,觉得手中的犀角蜡烛散发出的光晕,令我很是不舒服,尤其是眼睛,看久了感觉脑袋都开始发昏。
一只手从旁侧伸过来,修长的指节捏住烛台的底端,黑瞎子从我手中接过烛台,另一手往我鼻梁上戴了副墨镜,还顺手拍了拍我的脑门,语气平静,小孩子不要过度用眼,容易近视。我默默扶正墨镜,我才不是小孩,再过几个月我就虚岁18了。
莹绿色的烛光移动着,替我描绘出整扇门的模样。黑瞎子仅是轻轻一推,那扇本不该存在的门就嚯地开了,露出后边黑漆漆的口子,黑暗的不见一丝光亮。戴墨镜的男人眉梢一挑,转头把烛台放回高台,随即一脚踏在门槛上。他回头侧过半个身子,一手放在身后微微欠身,另一手伸到朝我身前,就像是像是童话里邀请公主跳舞的王子。
这人也许是那个掳走公主的海盗,隔着墨镜,我只能看到他上扬的嘴角。这人似乎很乐衷于搞点乱七八糟的仪式感,或许真如他所说,苦中作乐是他的爱好。我们要进到画里去了,你准备好了吗?公主,当然,我把手搭了上去,嘴角上扬,这个公主一定是自愿被掳走的。我想。







